王安忆、黄子平和吴亮三人谈:写小说就像织毛衣

----王安忆、黄子平和吴亮三人谈:写小说就像织毛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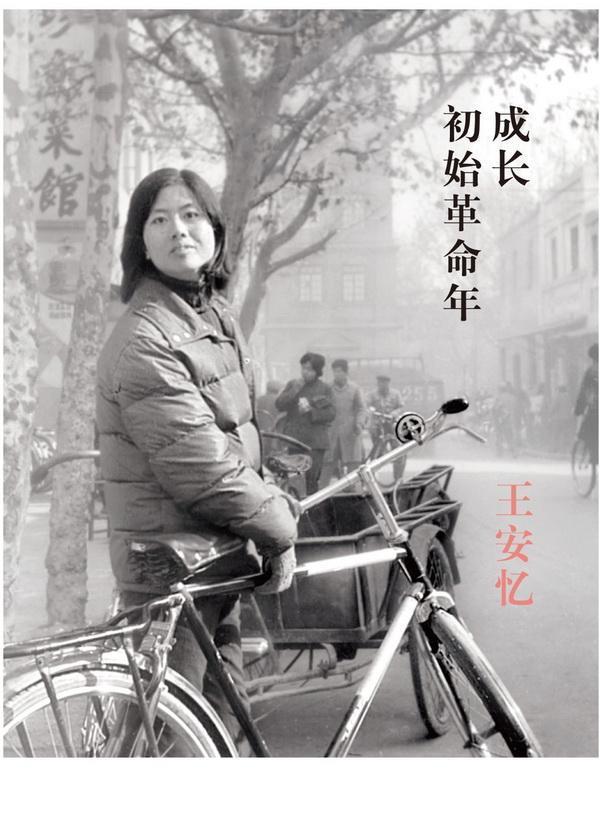
"multi_version":false
\r\n
特别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网友提供或互联网,仅供参考,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王安忆、黄子平和吴亮三人谈:写小说就像织毛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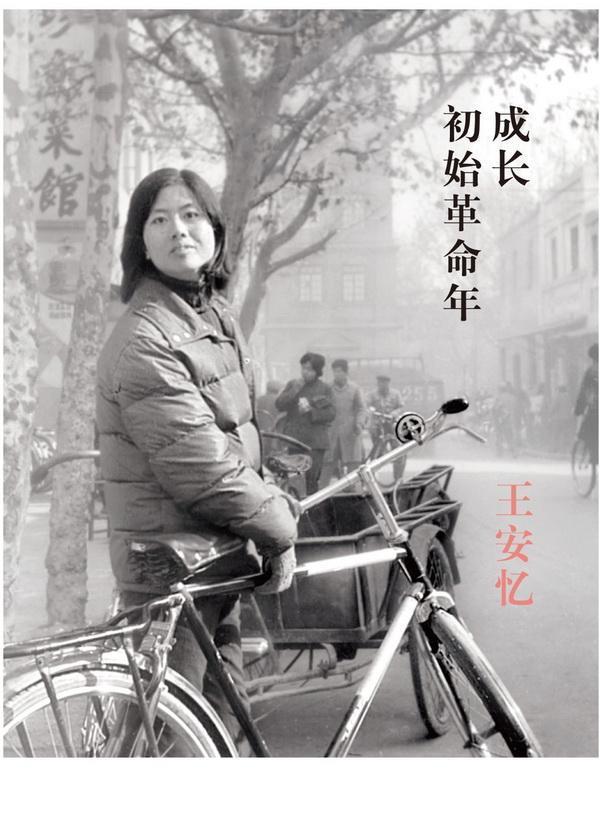
\r\n
特别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网友提供或互联网,仅供参考,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