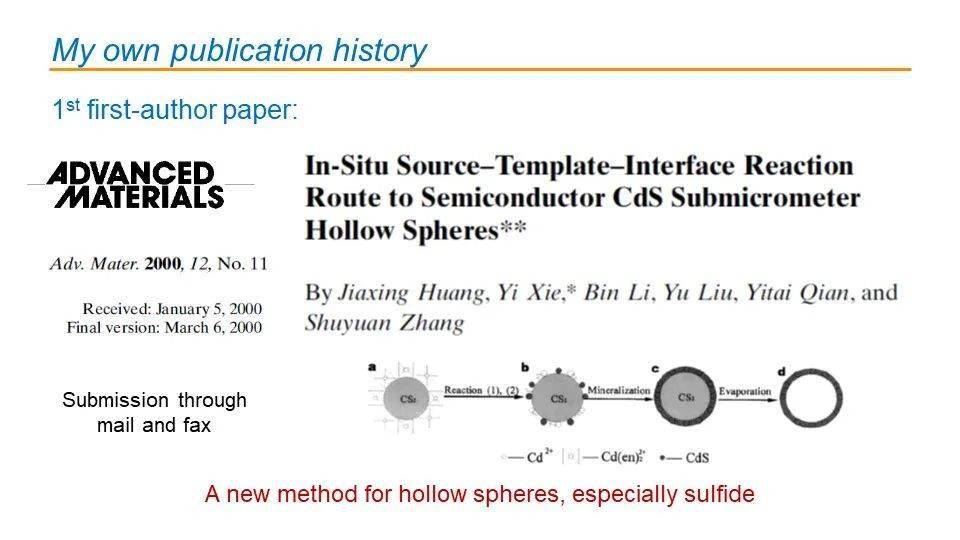
文章图片
那么回头看 , 这些文章的意义在哪里?它们没有带来重大的技术革新 , 也没有带来理论突破 , 肯定没有改变世界 , 但它们的确在科学文献中记录了一个个新合成方法 , 为后人提供了参考 。
对我个人来讲 , 这些经历给了我人生中一个巨大的正面激励 , 为我今后的科研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历练 。 那些论文 , 按今天流行的观点看 , 多属于“低影响 , 或低影响因子论文” , 但是那些论文却让好多人在这个过程中接受了人生第一次虽不完美 , 但却相对完整的科研训练 , 为后来国内科学研究的迅速上升提供了人才储备 。
02
读博阶段发论文
成为别人的垫脚石
后来我到了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博士 , 一开始做的是导师给的题目 , 磨了两年多 , 做得很纠结 , 差点就被虐到转学 。
好在这个过程中 , 我的“真爱”出来了——我捣鼓出了一个导电高分子纳米纤维 , 这篇文章反而发表得更早 , 成了我在读博阶段的第一篇一作文章 , 发在美国化学会志JACS上 。 Science和美国化学工程新闻(C&E News)都为我们这个工作写了Highlight , 我自己后来也沿着这个方向出了几篇第一作者的文章 。 这是我的博士导师执教十几年来的第一篇JACS , 对我来说 , 这简直就是“人生巅峰”了 。

文章图片
当时很多人觉得我们运气好 , 这么简单的工作也能发JACS:it's a cute little synthesis , 说得我自己都这么觉得了 。 但是时间久了就发现 , 这篇文章有很多人在跟进 。
其实我们合成或制备新材料 , 方法学越简单、越普适 , 能吸引很多人跳进来跟着你做 , 这绝对是一个好事;如果你没有教会读者什么 , 也没有让人从你的工作中受益 , 即使发了Science、Nature这样的明星期刊 , 那是不是也多为自娱自乐?
Agnes Pockels是我个人很敬佩的一位18世纪自学成才的德国女科学家 , 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I learned to my great joy that my work is being used by others for their investigations” 。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都应该是后人的垫脚石 , 这应该是我们发表论文的一个基本目的 。
03
博后阶段发文章
学会啃硬骨头
我在UC Berkele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杨培东教授课题组做了三年博后 。
这是我在博后阶段的第一篇文章 , 我们发现飘在水表面的纳米颗粒在干燥过程中有时会自动排列成非常漂亮且规整的花纹 。 我记得第一次在扫描电镜下看到这些花纹大约是凌晨3点 , Berkeley的学生都喜欢半夜上山做电镜 , 因为白天电镜太忙了 。 我和同组的Franklin看完电镜 , 看着山下的夜景悲喜交加:这么漂亮的发现 , 但恐怕我们怎么也搞不明白的 。
杨老师作为导师 , 没有跟着我们一起退缩 , 我和Franklin每个周会都在纠结该跟杨老师讲什么 。 甚至投稿之后 , 对审稿人的意见 , 我们也觉得搞不定 , 就跑去跟杨老师说要不就算了吧 , 换个容易的期刊投投?杨老师没说话 , 我们倒有点自惭形秽了 , 咬咬牙再试试吧 。
当时有两个思路 , 一个是用蛮力 , 不用分析太多 , 野蛮重复它100次 , 应该总能弄出来吧?结果试到第10次的时候 , 我们就快崩溃了 。 后来觉得不行 , 要不我就试试认真理性地分析一下 ,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终于冷静下来 , 从头分析、猜想 , 又做了几个快速模拟实验 , 结果发现 , 我还真有可能抓到了关键问题的蛛丝马迹 。 我跟我带的本科生Steve说 , 要不要吃完晚饭之后陪我熬夜拼一把? 如果成功的话我第二天早上带你吃早饭去 , 吃很贵的那家早饭 。
特别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网友提供或互联网,仅供参考,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