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 , 就是它
这部分工作大体完成后 , 我再以林格氏液(Ringer’s solution)冲洗每个器官;这里所用的林格氏液是比照昆虫体内各种盐类浓度所调制的人工昆虫血浆 。 接下来我采用所能想出的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来制作一条人工小径 。 首先 , 我在蚂蚁觅食的玻璃板上靠近蚁窝出口的地方 , 滴几滴糖水 , 让成群工蚁聚拢过来 。 然后 , 当一切就绪 , 再逐一用削尖的桦木涂药棒捣碎每种器官 。 接着 , 我再把棒尖压在玻璃板上 , 用这些被压扁的半液体物质画出一条直线 , 这条直线由围聚的工蚁群开始 , 往蚁窝的反方向延伸 。
我先试后肠、毒腺以及塞满大半蚁腹的脂肪体 。 没有动静 。 最后 , 我测试杜氏(Dufour’s gland) 。 这是一种手指形状的微小构造 , 科学界对于它的相关数据几乎是一无所知 , 只知道它是通往蚂蚁刺针基部的一根导管 , 而这根管子是运送毒液到体外的通路 。 杜氏腺内会不会含有留下踪迹记号的费洛蒙呢?没错 , 它真的有 。
蚁群的反应非常强烈 。 我原本期待看见几只工蚁很悠闲地离开糖水液 , 试探着看看新踪迹的尽头有些什么好东西 , 结果 , 我得到的却是好几打兴奋不已的蚂蚁 。 只见它们争先恐后踏上我为它们准备的路径 。 它们一边跑动 , 一边左右晃动头上的触角 , 侦测在空气中蒸发及扩散的分子 。 走到小径末端后 , 它们乱成一团 , 忙着搜寻其实并不存在的奖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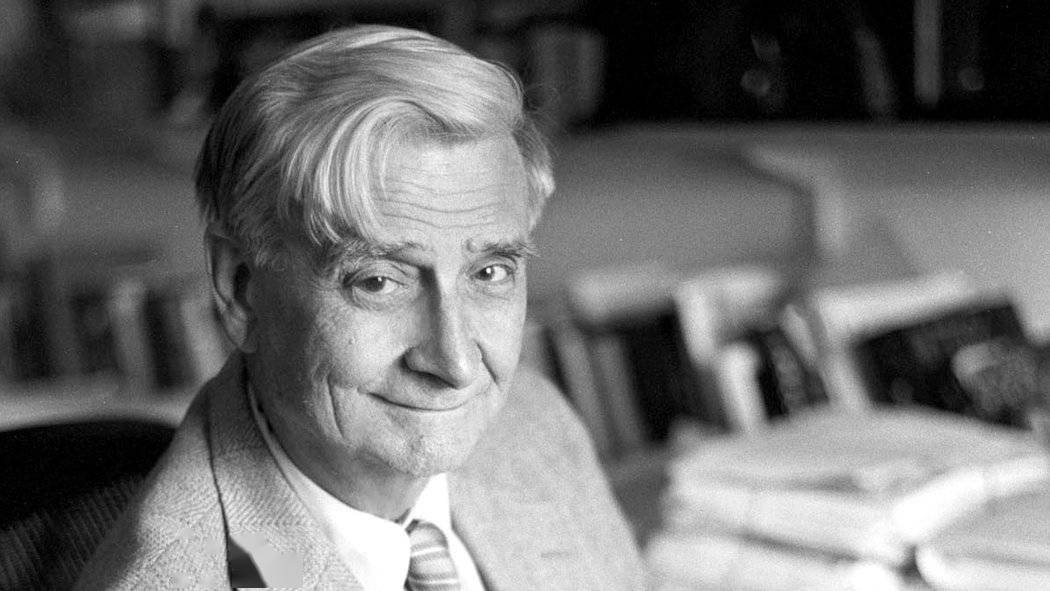
文章图片
威尔逊旧照 。
那天晚上 , 我完全无法入睡 。 这个灵感耽搁了5年 , 最后竟然在几个小时内就大有斩获——我找出了第一个与蚂蚁沟通有关的腺体!不仅如此 , 我还发现了化学通信里的全新现象 。 存在于该腺体内的费洛蒙 , 不只是工蚁觅食时的路标 , 而且就是觅食信号本身——在觅食过程中 , 该费洛蒙既是命令也是引导 。 化学物质就是一切 。 而生物检定(bioassay)的步骤也立刻变得容易多了 。 我很快乐地认识到 , 不必再为了想要得到的结果而费心安排一大堆混杂了众多其他刺激实验的设计 。 只要先做一个有效且容易测量的行为试验 , 生物学家和化学家搭档 , 就可以直接切入研究费洛蒙的分子结构了 。 假使其他费洛蒙(例如引发警戒及聚集行为的费洛蒙)的作用方式也和踪迹信息素一样的话 , 我们将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出大部分蚂蚁所使用的化学词语 。
接下来那几天我一再重复证明该踪迹费洛蒙的效用 。 在科学研究中再没有比重复做一个实验而实验又每次都会成功更令人愉快的了 。 当我把路径画到蚁窝入口时 , 蚂蚁立刻倾巢而出 , 即使我这么做的时候并没有先提供食物给它们 。 此外 , 当我把一滴由许多蚂蚁制成的杜氏腺浓缩液洒落到蚁窝时 , 工蚁涌出的比例相当高 , 而且它们显然是为了寻找食物 , 才散向四面八方 。
与火蚁群奋战
接下来我找了哈佛大学的化学家朋友约翰·劳(John Law)来帮忙鉴定踪迹信息素的分子结构 。 同时 , 还有另一位很有天分的大学部学生沃尔什(Christopher Walsh) , 也加入了我们这个研究小组 。 沃尔什后来成为顶尖的分子生物学家 , 并当上了达纳法伯癌症中心(Dana Farber Cancer Institute)的所长 。
我们算是一个阵容强大的组合 , 但是遭遇到了意料之外的技术难题:我们发现 , 不论何时 , 每只蚂蚁体内杜氏腺里的关键物质均少于十亿分之一克 。 不过 , 这问题也并非无法解决 。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期 , 正是好几种气相色谱法(gaschromatography)以及质谱分析法(massspectrometry)初露曙光之时 , 运用这类技术 , 可以鉴定百万分之一克的微量有机物质 。 换句话说 , 我们总共需要数万到数十万只蚂蚁 , 然后把它们的踪迹费洛蒙汇集起来 , 才能够凑足分析实验所需的最低剂量 。
特别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网友提供或互联网,仅供参考,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